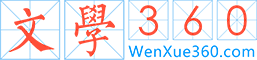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栾城应诏集》第九卷(苏辙·进策五道)
《栾城应诏集》第九卷(苏辙·进策五道)
《民政上》苏辙
○第一道
臣闻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
贤人君子,自洁于上,而民不免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如礼,而民不免为盗贼,礼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于下而不能止。
此犹未免为王道之未成也。
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
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悌廉耻之际。
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
强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
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
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祸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
天下之乱,盗贼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乐业,此其祸起于民之不相爱,而弃其孝悌廉耻之节。
夫自喜,则虽有太劳而其事不迁;相爱,则虽有强很之心,而顾其亲戚之乐,以不忍自弃于不义。
此二者,王道之大权也。
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
山林饥饿之民,皆有盗跖趑趄之心,而闺门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友。
朝廷之上,难有贤人,而其教不逮于下。
是故士大夫之间,莫不以为王道之远而难成也。
然臣窃观三代之遗文,至于《诗》,而以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难者。
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为此之味也。
故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耘播种之势,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实,妇子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
故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
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或来瞻女,载筐及筥。
其饟伊黍,其笠伊纠。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
当此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馌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业。
而其终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积之栗栗。
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以开百室,百室盈止。
妇子宁止,杀时犉牡。
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当此之时,岁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以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岁。
则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尽力者有以轻用其力,而狼戾无亲之人有所慕悦,而自改其操。
此非独于诗云尔,导之使获其利,而教之使其乐,亦如是云。
且民之性固安于所乐,而悦于所利。
此臣所以为王道之无难者也。
盖臣闻之,诱民之势,远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与竞。
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迁善之心,此岂非其远而难至者哉?明择郡县之吏,而谨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顽民不悛。
夫乡党之民,其视郡县之吏,自以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于前,不为之愧。
此其势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隐慝。
此岂非其近而无所与竞者邪?惟其里巷亲戚之间,幼之所与同戏,而壮之所以共事,此则其所与竞者也。
臣愚以为,古者郡县有三老、啬夫,今可使推择民之孝悌、无过、力田不惰、为民之素所服者为之。
无使治事,而使讥诮教诲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
而岁时伏腊,郡县颇置礼焉以风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强不服之心。
今不従民之所与竞而教之,而従其所素畏。
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
故教天下自所与竞者始,而王道可以渐至于下矣。
○第二道
臣闻三代之盛时,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洁,以求为君子。
父子相爱,兄弟相悦,孝悌忠信之美,发于士大夫之间,而下至于田亩,朝夕従事,终身而不厌。
至于战国,王道衰息,秦人驱其民,而纳之于耕耘战斗之中,天下翕然而従之。
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争首,以力搏力,进则有死于战,退则有死于将,其患无所不至。
夫周秦之间,其相去不数十百年。
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独喜于战攻,虽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窃知其故也。
夫天下之人,不能心知礼义之美,而亦不能奋不自顾以陷于死伤之地。
其所以能至于此者,其上之人实使之然也。
然而闾巷之民,劫而従之,则可以与之侥幸于一时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远。
而周秦之风俗,皆累世而不变,此不可不察其术也。
盖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闻于乡党而达于国人者,皆得以登于有司。
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得以自复其役,上者优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属其乡里。
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则皆争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兴,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无以异于周之所以使天下。
何者?至便之势所以奔走天下,万世之所不易也。
而特论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实在于民昏而不知教。
然臣以为,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
且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国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与为爱,而朋友欲其相与为信,临财欲其思廉,而患难欲其思义,此诚天子之所欲于天下者。
古之圣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
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求称其意。
今有人使人为之牧其牛羊,将责之以其牛羊之肥,则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
使夫牧者趋其所利而従之,则可以不劳而坐得其所欲。
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于樵苏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赏罚之轻重,则夫牧人将为牧邪?将为樵邪?为樵,则失牛羊之肥;而为牧,则无以得赏。
故其人举皆为樵,而无事于牧。
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后樵之为得,此无足怪也。
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于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爵禄。
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然天子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
是以若此不可却也。
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于一日之试,天下尚谁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试之可耻而不为者?《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
臣以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开之以利而作其怠,则天下必有应者。
今间岁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于其中。
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其所为求之者,止于其目之所见。
是以尽力于科举,而不知自反于仁义。
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
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
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
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欤!
○第三道
臣闻圣人将有以夺之,必有以予之,将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
纳之于正,而无伤其心,去其邪僻,而无绝其不忍之意。
有所矫拂天下,大变其俗,而天下不知其为变也。
释然而顺,油然而化,无所龃龉,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
盖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纷乱而至于不可告语者,非今世而然也。
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后食其粟,蚕缫而后衣其帛。
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获其报,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亲,则尽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则致力于友悌之节;欲求夫妇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务其所以致之之术。
故民各治其生,无望于侥幸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
凡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
至其不幸而死,其亲戚子弟又为之死丧祭祀、岁时伏腊之制,所以报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
笾豆簠簋、饮食酒醴之荐,大者于庙,而小者于寝,荐新时祭,春秋不阙。
故民终三年之忧,而又有终身不绝之恩爱,惨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报也。
至于后世则不然。
民怠于自修,而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皆归于鬼神冥寞之间,不知先王丧纪祭祀之礼。
而其所以追养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虚诞之说。
是以四夷之教,交于中国,纵横放肆。
其尊贵富盛拟于王者,而其徒党遍于天下,其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侈于天下之民。
而中国之人、明哲礼义之士,亦未尝以为怪。
幸而其间有疑怪不信之心,则又安视而不能去。
此其故何也?彼能执天下养生报死之权,而吾无以当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
盖天下之君子尝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远复其故。
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悦于民者甚佞。
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终不能服天下之意。
天下之民以为养生报死皆出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绝其教。
欲纳之于正而伤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绝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従之也甚难。
闻之曰:“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
作乎此者,必有以动乎彼也。”
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老之道,而悦乎养生报死之术。
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之实,而去其所悦之名,则天下何病而不従?盖先王之教民养生有方,而报死有礼。
凡国之赏罚黜陟,各当其处,贫富贵贱,皆出于其人之所当然。
力田而多收,畏法而无罪,行立而名声发,德成而爵禄至。
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获福之因,故无惑于鬼神。
而其祭祀之礼,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孙之意者,非有卤莽不详之意也。
故孝子慈孙有所归心,而无事于佛老。
臣愚以为,严赏罚,敕官吏,明好恶,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庙,严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报不得乘隙而制其死。
盖汉、唐之际,尝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说未去;尝有去者矣,而赏罚不详、祭祀不谨,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复反其旧。
今者国家幸而欲减损其徒,日朘月削将至于亡。
然臣愚恐天下尚犹有不忍之心。
天下有不忍之心,则其势不可以久去。
故臣欲夺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无憾于见夺,而日安其新。
此圣人所以变天下之术欤!
○第四道
臣闻管子治齐,始变周法,使兵民异处。
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而士乡十五。
制鄙以为五属,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之政。
国中之士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农不知战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
兵以卫农,农以资兵。
发兵征行,暴露战斗,而农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沾体涂足,而士卒不知其劳。
当是之时,桓公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零支,斩孤竹;西攘白狄,逾大行,渡辟耳之溪。
九合诸侯,筑夷仪,城楚丘,徜徉四方。
国无罢敝之民,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
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为之唱谋,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而不得反顾而为农。
阴诱六国之民,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而无战攻守御之役。
二者更相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
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应;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
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谋也。
自管仲死,其遗谋旧策,后世无复能用,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废。
何者?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
今夫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战斗之患。
此人之情,谁不可者?然当今天下之事,与管仲、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
古者霸王在上,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地利已尽,而民未乏困,当此之时,谓之人有余。
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莠实尽其利,人不得以为食,禽兽之所蕃息,当此之时,谓之地有余。
古之圣人,人有余,则务在于使人,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而举无废功。
地有余,则务在于辟地,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而举无遗力。
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余,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不已过哉!臣观京师之兵,不下数十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千人为辈,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此亦已侈于使人矣。
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是谓逆天而违人。
昔齐桓之世,人力可谓有余矣,而十五乡之士不过三万,车不过八百乘。
何者?惧不能久也。
方今天下之地,所当厚兵之处,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
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远国或数千里,以为远人险诐,未可以尽知其情也,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镇服其乱心。
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远,遂莫之变。
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乡,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而特病其不知战。
故今世之患,在不教乡兵,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
且天下治平,非缘边之郡,则山林匹夫之盗,及其未集而诛之,可以无事于大兵。
苟其有大盗,则其为变,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
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备之处,乃当厚其士兵以代之耳。
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乐战。
今之为兵之人,夫岂皆乐乎为兵哉?或者饥馑困踬,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
盖其间常有思归者矣。
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以减屯戍之兵,虽使去者太半,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
盖古者有余则使之以宽,而不足则使之以约。
苟必待其有余,而后能办天下之事,则无为贵智矣。
○第五道
臣闻近代以来,天下之变备矣。
世之君子随其破败而为之立法,补苴缺漏,疏剔棼秽,其为法亦已尽矣,而后世之弊常不为之少息。
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暂享其利而不能久。
因循维持至于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独受其责,其病最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遗策,又莫不尽废而不举,是以为国百有余年而不至于治平者,由此之故也。
盖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
田制一败,而民事大坏,纷纷而不可止。
其始也,兼并之民众而贫民失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以势相役,收太半之税。
耕者穷饿,而不耕者得食。
以为不便,故従而为之法曰:限民名田,贵者无过若干,而贫者足以自养。
此董生之法也。
天下之人,兼并而有余,则思以为骄奢。
骄奢之风行于天下,则富者至于破其资畜,而贫者耻于不若,以争为盗而不知厌。
民皆有为盗之心,则为之上者甚危而难安,故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过,而少者无所慕也,以平风俗。
此贾生之法也。
民之为性,丰年食之而无余,饥年则转死沟壑而莫之救。
富商大贾乘其不足而贵卖之,以重其灾,因其有余而贱取之,以待其敝。
予夺之柄归于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为敛,藜藿不继而不为发,故为之法曰:贱而官为籴之,以无伤农,贵而官为发之,以无伤末。
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
此李悝之法也。
古者三代之兵,出而为兵,入而为长。
出兵临敌,则国有资粮之忧;而兵罢役休,则无复养兵之费。
及至后世,海内多故,而征伐不息,以为害农,故特为设兵以办天下之武事。
其始若不伤农者,而要其终衣食之奉,农亦必受其困,故为之法曰:不战,则耕以自养,而耕之闲暇,则习为击刺,以待寇至。
此赵充国之法也。
盖古之遗制,其不可施于今者甚多。
而臣不敢复以为说,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
未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欤?臣闻事固有可以无术而行者,有时异事变,无术而不可行者。
均民以名田,齐众以立制,是无术而可以直行者也。
平籴以救灾,屯田以宽农,是无术而不可行者也。
古者贤君在上,用度足而财不竭,捐其有余,以备民之所不足,而不害于岁计。
今者,岁入不足以为出,国之经费犹有所不给,而何暇及于未然之备?古者将严而兵易使,其兵安于劬劳,故虽使为农而不敢乱。
今者天下之兵,使之执劳者,皆不知战,而可与战者,皆骄而不可使,衣食丰溢,而筋力罢惫,且其平居自处甚倨,而安肯为农夫之事?故屯田平籴之利,举世以为不可复者,由此之故也。
曷亦思其术矣?臣尝闻之:贾人之治产也,将欲有为而无以为资者,不以其所以谋朝夕之利者为之也。
盖取诸其不急之处而蓄之,徐徐而为之,故其业不伤而事成。
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余之取于民者,亦非其正矣。
茶盐酒铁之类,此近世之所设耳。
夫古之时,未尝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为国亦无所乏绝。
臣愚以为可于其中择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岁以为平籴之资,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余,则不复有所顾惜,而发之也轻。
发之也轻,而后民食其利,其与今之所谓常平者,亦已大异矣。
抑尝闻之,人之牧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
马彘之相去未能几也,而犹且不可使。
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为农,此其不従,固无足怪者。
今欲以兵屯田,盖亦告之以将屯田而募焉。
人固有无田以为农而愿耕者,従其愿而使之,则虽劳而无怨。
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则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复补,以待其自衰矣。
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尽矣,而其守法者,常至于怠惰而不举。
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于今者,而不求古之遗法而依之以为治,可不大悲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