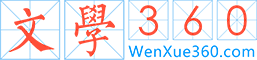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栾城三集》第十卷(苏辙·记四首)
《栾城三集》第十卷(苏辙·记四首)
《遗老斋记》
庚辰之冬,予蒙恩归自南荒,客于颍川,思归而不能。
诸子忧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侪之责也。”
则相与卜筑,五年而有成。
其南修竹古柏,萧然如野人之家。
乃辟其四楹,加明窗曲槛,为燕居之斋。
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颍滨遗老也,盍以“遗老”名之?汝曹志之。
予幼従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
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
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
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
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
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
及宣后临朝,擢为右司谏。
凡有所言,多听纳者。
不五年,而与闻国政,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
然其间与世俗相従,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虽号为得志,而实不然。
予闻之乐莫善于如意,忧莫惨于不如意。
今予退居一室之间,杜门却扫,不与物接。
心之所可,未尝不行;心所不可,未尝不止。
行止未尝少不如意,则予平生之乐,未有善于今日者也。
汝曹志之,学道而求寡过,如予今日之处遗老斋可也。
《藏书室记》
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
今老矣,犹志其一二。
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
此孔氏之遗法也。”
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
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盖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及其安之,然后申之以弦歌,广之以读书。
曰:“道在是矣。
仁者见之,斯以为仁;智者见之,斯以为智矣。”
颜、闵由是以得其德,予、赐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
譬如农夫垦田,以植草木,小大长短,甘辛咸苦,皆其性也,吾无加损焉,能养而不伤耳。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
如孔子犹养之以学而后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
傅说之诏其君,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
“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而况余人乎?子路之于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于学,尝谓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非之曰:“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凡学而不读书者,皆子路也。
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败,与所遇之可否,未有不为病者。
虽然,孔子尝语子贡矣,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
非欤?”曰:“非也。
予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非多学之所能致,则子路之不读书,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谓也。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贯之者,可得而见也。”
孟子论学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心勿忘,则莫如学,必有事,则莫如读书。
朝夕従事于诗书,待其久而自得,则勿忘勿助之谓也。
譬之稼穑,”“为无益而舍之,则不耘苗者也;助之长,则揠苗者也。”
以孔孟之说考之,乃得先君之遗意。
《待月轩记》
昔予游庐山,见隐者焉,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犹日也,身犹月也。”
予疑而诘也。
则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
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
日出于东。
方其出也,物咸赖焉。
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
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未始有变也。
惟其所寓,则有盈阙。
一盈一阙者,月也。
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
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
惟其所寓,则有死生。
一生一死者身也。
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
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
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此术也,而合于道。
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
予异其言而志之久矣。
筑室于斯,辟其东南为小轩。
轩之前廓然无障,几与天际。
每月之望,开户以须月之至。
月入吾轩,则吾坐于轩上,与之徘徊而不去。
一夕举酒延客,道隐者之语,客漫不喻曰:“吾尝治术矣,初不闻是说也。”
予为之反复其理,客徐悟曰:“唯唯。”
因志其言于壁。
《坟院记》
旌善广福禅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赠司徒坟侧精舍也。
先公既壮而力学,晚而以德行文学名于世。
夫人程氏,追封蜀国太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有二子,长曰轼,季则辙也。
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
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辙兄弟虽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几五十,乃始得还朝。
兄气刚寡合,已入复出。
辙碌碌无能轻重,五年而至尚书右丞,与闻国政,以故事得于坟侧建刹度僧,以荐先福。
坟之东西四里许,有故伽蓝,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
相传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舍也。
辙以请于朝,改赐今榜,时元祐六年也。
既三年,兄弟皆罪废,南迁海上。
又六年,蒙思北归,兄至毗陵,以病没。
辙中止颍川,不能归。
又五年,前执政以黜去者,皆夺坟上刹。
又二年,上哀矜旧臣,手诏复还畀之。
坟之西南十余步有泉焉,广深不及寻,昼夜瀵涌,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
自辙南迁,而水日耗,至夺刹遂竭。
父老来告,辙惕焉。
疑获谴于幽明,徬徨不知所为。
而手诏适至,泉亦滃然而复。
山中人皆曰:“诏书乃与天通耶?”辙闻之,溯阙而拜,以膺上赐。
久之,乃为之记,使世子孙知兹刹废兴所自,以无忘朝廷之德。
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护军、栾城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苏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