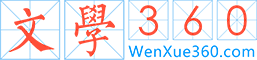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栾城应诏集》第四卷(苏辙·进论五首)
《栾城应诏集》第四卷(苏辙·进论五首)
《礼论》苏辙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
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而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
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心,盎然见于其面,而坌然发于其躬。
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
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
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
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
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盖常有巢居穴处,污樽坏饮、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
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
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爓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
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懦而不决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韨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
宗庙之际,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
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従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
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
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
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
虽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
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
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
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
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従鬼神之所安。
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従其器。
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従其所安焉耳。
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祥,则遂以为不可。
盖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従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论》苏辙
《易》者,卜筮之书也。
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
然《易》始于卦,而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
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
此高论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阔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今夫《易》之所谓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
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
此四数乾,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
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而其次极于七,故七为少而九为老。
至于老阴,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则老阴当十,而少阴当八,今少阴八,而老阴反当其下之六,则又为之说曰:阴不可以有加于阳,故抑而处之于下。
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而曷有曰老阴八,而少阴六?且夫阴阳之数,此天地之所为也,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此其尤不可者也。
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
《易》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为夫揲蓍之故也。
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
揲蓍之法曰:卦一归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数之。
得九而以为老阳,得八而以为少阴,得七而以为少阳,得六而以为老阴。
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
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
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乾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
天下之物,以少为主,故乾之子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
老阴、老阳者,乾坤是也;少阴、少阳者,乾坤之子是也。
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
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
多少者,奇偶之象也。
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
阴阳之老少,于卦见之于爻,而于爻见之于揲。
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则夫此三揲者,区区焉分其少多而各为之处,果何以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异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
三揲而皆多,此无以异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
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异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
三揲而多者一,此无以异于《巽》《离》《兑》之一偶而二奇也。
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之所在,不可强以为说也。
《书论》苏辙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定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劓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
曰:嗟夫!世俗之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终。
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下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亹而不倦,必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従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従事。
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者。
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従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
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以求曲直之当,亦无足怪者。
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
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子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莫肯听。
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従?而其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従。
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
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
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
既又恐其不従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
’”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
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于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
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决。
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者也。
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
及其不可听,则又反复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
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苏辙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
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
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
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
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
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
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
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今《诗》之传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
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喓々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
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
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
盖其为学亦以劳矣。
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
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
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
《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
此非有所取乎靁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
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
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
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苏辙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
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
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
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
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
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
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
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
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
此其大凡也。
《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
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
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
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
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
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
此所谓急之之言也。
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
《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
而以为卫伐凡伯。
《春秋》书曰:“齐仲孙来。”
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
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
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
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