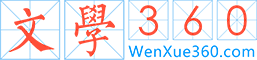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苏轼集》第七十五卷(书二十首)
《谢欧阳内翰书》苏轼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
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
纷纷肆行,莫之或禁。
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
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
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
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
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
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
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
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
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
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
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
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
不宣。
《谢梅龙图书》苏轼
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
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
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
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
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
后之世风俗薄恶,惭不可信。
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
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
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
夫惟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
伏惟龙图执事,骨鲠大臣,朝之元老。
忧恤天下,慨然有复古之心。
亲较多士,存其大体。
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
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仓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
故君子以为近古。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
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人之幸遇,乃有如此。
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谢范舍人书》苏轼
轼闻之古人,民无常性。
虽土地风气之所禀,而其好恶则存乎其上之人。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
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
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
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
弦歌之声,与邹、鲁比。
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
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
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涂。
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
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
比之西刘,又以远过。
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
则其他可知矣。
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执事与梅公之于蜀人,其始风动诱掖,使闻先王之道,其终度量裁置,使观天子之光,与相如、王褒,又甚远矣。
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谨因阍吏进拜于庭,以谢万一。
又以贺执事之乡人得者之多也。
《上王兵部书》苏轼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
执事以高才盛名,作牧如此,盖亦尝有以相马之说告于左右者乎?闻之曰:骐骥之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动,其足如无所着,升高而不轾,走下而不轩。
其技艺卓绝而效见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识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责其技也。
夫马者,有昂目而丰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后之兔,远望目若视日而志不存乎刍粟,若是者飘忽腾踔,去而不知所止。
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达之衢,一目而眄之,闻其一鸣,顾而循其色,马之技尽矣。
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
士之贤不肖,见于面颜而发泄于辞气,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间,而必曰久居而后察,则亦名相士者之过矣。
夫轼,西州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
其足迹偶然而至于执事之门,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
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
且执事何修而得此称也?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者,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衢,而庶几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尔。
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
轼将自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进。
不宣。
轼再拜。
《与刘宜翁书》苏轼
轼顿首宜翁使君先生阁下。
秋暑,窃惟尊体起居万福。
轼久别因循,不通问左右,死罪!死罪!愚暗刚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
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复道也。
惟有一事,欲谒之先生,出于迫切,深可悯笑。
古之学者,不惮断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则过矣。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
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无一事,胸中廓然,实无荆棘。
窃谓可以受先生之道。
故托里人任德公亲致此恳。
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术,但以人无受道之质,故不敢轻付之。
轼虽不肖,窃自谓有受道之质三,谨令德公口陈其详。
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见闻此,欣然拊掌,尽发其秘也。
幸不惜辞费,详作一书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专遣人至惠州。
路远,难于往返咨问,幸与轼尽载首尾,勿留后段以俟愤悱也。
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枣者,亦望不惜分惠。
迫切之诚,真可悯笑矣。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然先生笔端有口,足以形容难言之妙,而轼亦眼中无障,必能洞视不传之意也。
但恨身在谪籍,不能千里踵门,北面抠衣耳。
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嵝令,先生倘有意乎?峤南山水奇绝,多异人神药,先生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屦以从矣。
昨夜梦人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觉而占之,乃郭景纯为许迈筮,有“元吉自天佑之”之语,遽作此书,庶几似之。
其余非书所能尽,惟祝万万以时自重。
不宣。
《上王刑部书》苏轼
轼今日得于州吏,伏审执事移使湖北。
窃以江陵之地,实楚之故国,巴蜀、瓯越、三吴之出入者,皆取道于是,为一都会。
其山川之胜,盖历代所尝用武焉。
其间吴、蜀、魏氏尤悉力争之。
宋有天下,王师平高继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权,又皆出此。
其人才之秀,风物之美,有屈、宋、伍、祢之赋咏存焉。
建节旄而使者,专有是土。
其见倚之重,为吏之乐,岂细也哉。
然执事处之,则未足贺。
诚以执事之材力地望,宜进任于时,不宜任此。
或者以谓蛮反,南方用兵,湖北邻也,宜择人抚之,故以属执事。
使诚有是议,当出于庙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
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岂以位之彼此大小为择哉。
于执事之心,当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职而已,岂以位之彼此大小动吾意哉?固执事之所务也。
不宣。
轼再拜。
《与佛印禅老书》苏轼
轼启。
归宗化主来,辱书,方欲裁谢,栖贤迁师处又得手教,眷与益勤,感怍无量。
数日大热,缅想山门方适清和,法体安稳。
云居事迹已领,冠世绝境,大士所庐,已难下笔,而龙居笔势,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
幸稍宽假,使得款曲抒思也。
昔人一涉世事,便为山灵勒回俗驾,今仆蒙犯尘垢,垂三十年,困而后知返,岂敢便点涴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识,而迎许之,何以得此,岂非宿缘也哉。
向热,顺时自爱。
不宣。
轼再拜。
收得美石数百枚,戏作《怪石供》一篇,以发一笑。
开却此例,山中斋粥今后何忧,想复大笑也。
更有野人于墓中得铜盆一枚,买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结缘也。
《上荆公书》苏轼
轼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
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
别来切计台候万福。
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
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
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
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
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一数也。
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
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秋气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顺时候,为国自重。
《上韩枢密书》苏轼
轼顿首上枢密侍郎阁下。
轼受知门下,似稍异于寻常人。
盖尝深言不讳矣,明公不以为过。
其在钱塘时,亦蒙以书见及,语意亲甚。
自尔不复通问者,七年于兹矣。
顷闻明公入西府,门前书生为作贺启数百言。
轼辄裂去,曰:“明公岂少此哉!要当有辅于左右者。”
昔侯霸为司徒,其故人严子陵以书遗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
世以子陵为狂,以轼观之,非狂也。
方是时,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满,有轻人臣之心,躬亲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
霸为司徒,奉法循职而已,故子陵有以感发之。
今陛下之圣,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贤,亦远过侯霸。
轼虽不用,然有位于朝,未若子陵之独善也。
其得尽言于左右,良不为过。
今者,贪功侥幸之臣,劝上用兵于西北。
使斯言无有,则天下之幸,孰大于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争也。
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计之详矣,明公亦必然之,轼不敢复言。
独有一事,以为臣子之忠孝,莫大于爱君。
爱君之深者,饮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孙多,长有天下。”
此岂非臣子之愿欤?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
出而无功,与有功而君不贤者,皆不足道也。
其贤而有功者,莫若汉武帝、唐太宗。
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见,其长亘天。
后遂命将出师,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
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之后,师行盖十余年,兵所诛夷屠灭死者不可胜数。
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
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
唐太宗既平海内,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且犹未厌,亲驾征辽东。
当时大臣房、魏辈皆力争,不从,使无幸之民,身膏草野于万里之外。
其后太子承乾、齐王佑、吴王恪,皆相继诛死。
其余遭武氏之祸,残杀殆尽。
武帝好古崇儒,求贤如不及,号称世宗。
太宗克己求治,几致刑措,而其子孙遭罹如此。
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祸者,既足以为后嗣之累,则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为子孙之福,审矣。
轼既无状,窃谓人主宜闻此言,而明公宜言此。
此言一闻,岂惟朝廷无疆之福,将明公子孙,实世享其报。
轼怀此欲陈久矣,恐未信而谏,则以为谤。
不胜区区之忠,故移致之明公。
虽以此获罪,不愧不悔。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上吕相公书》苏轼
轼昨日面论邢夔事。
愚意本谓刑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为盗杀之,苟用犯时不知勿论法,深恐今后欲杀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杀,但云“我意汝是盗”即免矣。
公言此自是谋杀,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轼归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课儿于大醉不省记中,打杀南贵,就缚,至醒,取众证为定,作可悯奏,已得旨贷命,而门下别取旨断死。
窃闻舆议,亦恐贷之启奸,若杀人者得以醉免,为害大矣。
轼始者亦以为然,固已书过录黄,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后实醉不醒而杀,其情可悯,可以原贷,若托醉而杀,自是谋杀,有勘司在。
邢夔犯时不知,秦课儿醉不省记,皆在可悯之科,而邢夔臀杖编管,秦课儿决杀,似轻重相远,情有未安。
人命至重,若公以为然,文字尚在尚书省,可追改也。
《与章子厚书》苏轼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
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
即日,不审台候何似?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
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
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
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
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
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
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
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
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
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
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
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
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
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
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
俸入所得,随手辄尽。
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
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
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会见无期,临纸惘然。
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
《答刘巨济书》苏轼
轼启。
人来辱书累幅,承起居无恙。
审比来忧患相仍,情怀牢落,此诚难堪。
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当深计远虑,不应戚戚徇无已之悲。
贤兄文格奇拔,诚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当以累足下。
见其手书旧文,不觉出涕。
诗及新文,爱玩不已。
都下相知,惟司马君实、刘贡父,当以示之。
恨仆声势低弱,不能力为发扬。
然足下岂待人者哉!《与吴秀才书》论佛大善。
近时士人多学谈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
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
仆老拙百无堪,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可羞愧,以此得虚名。
天下近世进人以名,平居虽孔孟无异,一经试用,鲜不为笑。
以此益羞为文。
自一二年来,绝不复为。
今足下不察,犹以所羞者誉之,过矣。
舍弟差入贡院,更月余方出。
家孟侯虽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
其兄安国亦然。
勤国亦捷州解,皆在此。
因风时惠问,以慰饥渴。
何时会合,临纸怅然。
惟强饭自重。
《与孙运勾书》苏轼
轼启。
脾能母养余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
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
太仓公言安谷过期,不安谷不及期。
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
近见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状貌气力如四五十人。
问其所得,初无异术,但云平生习不饮汤水耳。
常人日饮数升,吾日减一合,今但沾唇而已。
脾胃恶湿,饮少,胃强气盛,液行自然,不湿。
虽冒暑远行,亦不念水,此可谓至言不繁。
闻曼叔比得肿疾,皆以利水药去之。
中年以后,一利一衰,岂可数乎?当及今无病时,力养胃气。
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
陈彦升云,少时得此病,服商陆、防已之类,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脐下,乃愈。
此亦固胃助阳之意也。
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术耳。
姜橘辣药,例能张肺,多为肿媒,不可服,有书以告之为佳也。
《与王庠书三首(之一)》苏轼
轼启。
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辅以药物,眷意甚厚。
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
罪戾远黜,既为亲友忧,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比其还家,几尽此岁,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
但喜比来侍奉多暇,起居佳胜。
轼罪大责薄,居此固宜,无足言者。
瘴疠之邦,僵朴者相属于前,然亦有以取之。
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
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
以此居之泰然。
不烦深念。
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
西汉以来,以文设科而文始衰,自贾谊、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况其下者。
文章犹尔,况所谓道德者乎?若所论周勃,则恐不然。
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
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
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
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
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抃不已。
应举者志于得而已。
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
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
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学,以卒远业。
相见无期,万万自重而已。
人还,谨奉手启,少谢万一。
《与王庠书三首(之二)》苏轼
轼启。
二卒远来,承手书两幅,问劳教诲,忧爱备尽。
仍审侍奉多暇,起居万福,感愧深矣。
轼罪责至重,上不忍诛,止窜岭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
来书开说过当,非亲朋相爱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诗,词气比旧益见奇伟,粲然如珠贝溢目。
非独乡闾世不乏人为喜,又幸珍材异产,近出姻戚,数日读不释手。
每执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
老朽废学久矣,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
足下犹欲使议论其间,是顾千里于伏枥也。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南迁以来,便自处置生事,萧然无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
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
非独以愈,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
初欲独赴贬所,儿女辈涕泣求行,故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散就衣食。
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
足下过相爱,乃遣万里相问,无状自取,既为亲友忧及,又使此两人者蒙犯瘴雾,崎岖往来,吾罪大矣。
寄遗药物并方,皆此中无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御瘴也。
轼为旧患痔,今颇发作,外无他故,不烦深念。
会晤无期,惟万万以时保练。
《与王庠书三首(之三)》苏轼
轼启。
前后所寄高文,无不达者。
每见增叹,但恨老拙无以少答来贶。
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声名于当时。
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
程夫子尚困场屋,王贤良屈于州县,皆造物有不可晓者。
海隅风土甚恶,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医无药,杜门食淡,不饮酒,亦粗有味也。
目昏,倦作书,又此信发书极多,不能尽。
察之!《答陈季常书》苏轼
轼启。
惠兵还,辱得季常手书累幅,审知近日尊候安胜。
择、括等三凤毛皆安,为学日益,喜慰无量。
轼罪大责薄,圣恩不赀,知幸念咎之外,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也。
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羡,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
岂欺我哉!自数年来,颇知内外丹要处。
冒昧厚禄,负荷重寄,决无成理。
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
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
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在定日作《松醪赋》一首,今写寄择等,庶以发后生妙思,着鞭一跃,当撞破烟楼也。
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
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
今日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
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
托郡中作皮筒送去。
想黄人见轼书,必不沉坠也。
子由在筠,极安。
处此者,与轼无异也。
书云,老躯极健,度去死远在。
读之三复,喜可知也。
吾侪但断却少年时无状一事,诚是。
然他未及。
子由近见人说,颜状如四十岁人,信此事不辜负人也。
不宣。
轼再拜。
《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
轼启。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
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
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又曰:“辞达而已矣。”
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
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
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
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
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
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
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
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
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
愈远。
惟万万以时自爱。
不宣。
《与孙知损运使书》苏轼
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
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
数年乃见效。
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
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
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
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
宜与永免冬教,又当有以优异劝奖之。
已条上其事,更月余可发。
此事行之边臣,无赫赫之功,然经久实事无如此者。
觇者多云可汗老疾,欲传雏,雏为人猜忌好兵,边人尽知之。
此岂可不留意。
愿公痛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书岂能尽也。
虏涵浸德泽久矣,其势亦未遽渝盟,但恐雏儿鸷忍,其下必有不忠贪功好利之人谋之,必先使北贼小小盗边,托为不知。
若不折其萌芽,狃于小利,张而不已,必开边隙。
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
所条上数事,亦甚稳帖,不至张皇。
惟乞免人户折变,所费不多。
及立闲名目,奖社人头首。
又乞复回易收息,时遣机宜僚属,费少钱粮,就地头赏其高强者耳。
《与王定国书》苏轼
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
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己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绝。
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芥蒂,然后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
扬州有侍其太保,官于烟瘴地十余年。
比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
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国自知之,更请加功不废。
每日饮少酒调食,令胃气壮健。
安道软朱砂膏,轼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
可久服。
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
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
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
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看破。
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勿轻用钱物。
一是远地,恐万一阙乏不继。
一是灾难中用贬恶,消厄致福之一端也。
又递中领手教,知已到官无恙,自处泰然,顿慰悬想。
知摄二千石,风声震于殊俗,一段奇事也。
轼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
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
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
二书反覆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
然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
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今见定国,每有书皆有感恩念咎之语,甚得诗人之本意。
仆虽不肖,亦当仿佛于庶几也。
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
宾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致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
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
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勾漏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
陈璨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此来。
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
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轼观之,唯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
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
迩来江淮间酷暑,殆非人所堪,况于岭外?唯道德清旷,必有以解烦释闷者。
入秋来翛然清远,计尊候安胜。
君学术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读史书,仍手自抄为妙。
造次!造次!轼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
今又下手作《书传》。
迂拙之学,聊以娱老,且以为子孙藏耳。
子由亦了得《诗传》,又成《春秋集传》,想知之,为一笑耳。
辱惠书并新诗、妙曲,大慰所怀。
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
得此佳作,终日喜快,滞闷冰释,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石,似可足食。
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