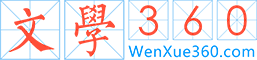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苏轼集》第六十三卷(奏议十三首)
《乞擢用林豫札子》苏轼
元祐七年十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窃谓才难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财赋,除盗贼,干边鄙,兴利除害,常有临事乏人之叹。
古人有言:“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
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
此古今之通患也。
臣伏见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为布衣,已有奇节,及其从事,所至有声。
其在涟水,屏除群盗,尤著方略。
其人勇于立事,常有为国捐躯之意。
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
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
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
取进止。
《乞赙赠刘季孙状》苏轼
元祐七年十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状奏。
臣等窃闻仁宗朝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众寡不敌,奸臣不救,平遂战殁,竟骂贼不食而死。
诏赠侍中,赐大第,官其诸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七人。
诸子颇有异材,而皆不寿,卒无显者。
家事狼狈,赐第易主。
独季孙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练达军政,至于忠义勇烈,识者以为有平之风。
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
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
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
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
臣等实与季孙相知,既哀其才气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间,而子孙沦替,不蒙收录,岂朝廷之意哉?今执政侍从多知季孙者,如加访问,必得其实。
欲望朝延特诏有司,优与赙赠,以振其妻子朝夕饥寒之忧,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孙,虽跨历岁月,朝廷犹赐存恤,于奖劝之道,不为小补。
季孙之子三班借职璨,见在京师,乞早赐指挥。
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
季孙身亡,合得送还人为般擎。
女婿两房,并已死尽。
其丧柩见在晋州,无由般归京师。
欲乞指挥晋州,候本家欲扶护归葬日,即与差得力厢军三十人,节级一人,般至京师。
《再论李直方捕贼功效乞别与推恩札子》苏轼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先知颍州日,为有剧贼尹遇、陈兴、郑饶、李松等,皆宿奸大恶,为一方之患。
而汝阴县尉李直方,本以进士及第,母年九十余,只有直方一子,相须为命,而能奋不顾身,躬亲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财,缉知余党所在,分遣弓手,前后捕获,功效显著。
直方先公后私,致所差人先获陈兴等三人,而直方躬亲,后获尹遇一名,与赏格小有不应。
臣寻具事由闻奏,乞以臣合转朝散郎一官特与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资酬奖。
后来朝旨,只与直方免试。
窃缘选人免试,恩例至轻,其间以毫发微劳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劝捐躯除患之士。
伏望圣慈,特赐检会前奏,别与推恩,仍乞许臣更不磨勘转朝散郎一官。
所贵余人难为援例。
取进止。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苏轼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
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买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
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
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
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
臣窃为圣世病之。
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茶之费;而蓄积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
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
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
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
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
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
又计籴本水脚官钱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
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
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
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
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
虽比今之法,小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
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谨具逐条如后。
《《天圣附令》》苏轼
诸商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
诸卖旧屋材柴草米面之物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
其卖诸色布帛不及匹而将出城,及陂池取鱼而贩易者,并准此。
《《元丰令》》苏轼
诸商贩谷及以柴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
(旧收税处依旧例。)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谷面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税。
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鱼非货易者,准此。
《《元祐敕》》苏轼
诸兴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纳力胜税钱。
(旧收税处依旧例,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斛斗并面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
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鱼非货易者,准此。
右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
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振救,官司省费,其利不可胜计。
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益见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苏轼
元祐七年南郊,轼为卤薄使导驾。
内中朱红车子十余两,有张红盖者,争道乱行于乾明寺前。
轼于车中草此奏。
奏入,上在太庙,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
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效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
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
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
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
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
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
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奏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来观,莫不悦服。
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
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干勾当人施行。
取进止。
《再荐宗室令畤札子》苏轼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
臣前任颖州日,曾论荐本州佥判承议郎赵令畤,儒学吏术,皆有过人,恭俭笃行,若出寒素。
意望朝廷特赐进擢,以风晓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
至今未蒙施行。
令畤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与外任差遣,臣窃惜之。
欲乞检会前奏,详酌施行。
取进止。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苏轼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字书,请详批印造,供赴当所交割。
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
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
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关,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
今来监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
其当行人吏上簿者。”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鬼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
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
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
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
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
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契丹用。
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
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
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称本朝正朔,却退其物。
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
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
及画一处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过当。
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
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
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
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
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
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差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移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
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
其乖(一作多)。
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
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
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礼部看详。
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谓:“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
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违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
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
不可予。”
诏从之。
臣窃以谓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心腹者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
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
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
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
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御览》何异?臣虽知前次曾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窃以谓前次本不当与,若便以为例,即上乖先帝遗旨,下与今来不赐《御览》圣旨异同,深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薄责,至为末事,于臣双无丝毫之损。
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小国,事必曲从,官吏苟循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
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
所以须至极论,仍具今来合处置数事如后。
一、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后并不得发舶往高丽,蒙已立条行下。
今来高丽使却搭附闽商徐积舶船入贡。
及行根究,即称是条前发舶。
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虽有条贯,实与无同。
欲乞特降指挥,出榜福建、两浙,缘海州县,与限半年内令缴纳条前所发公凭,如限满不纳,敢有执用,并许人告捕,依法施行。
.贴黄。
据陈轩所奏语录,即是高丽知此条。
今来高丽使所欲买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并不许收买。
.贴黄。
准都省批状指挥,人使所买书籍,内有《敕式》,若令外夷收买,事体不便,看详都省本为《策府元龟》及《北史》,前次已有体例,故以礼部并不检会为罪,未委《敕式》有何体例,一概令买?一、近日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薄一百贯,欲于杭州妆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
窃虑都省复以为罪。
窃缘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妆佛为名,久住杭州,搔扰公私。
窃闻近岁西蕃阿里库乞买金薄,朝廷重难其事,节次量与应副。
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迫,乞指挥馆伴,令以打造不出为词,更不令收买。
一、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抄写曲谱。
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
若画朝旨特为抄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
.贴黄。
臣前任杭州,不受高丽所进金塔,虽曾密奏闻,元只作臣私意拒绝。
兼自来馆伴使臣,若有所求请,不可应副,即须一面说谕不行,或其事体大,即候拒讫密奏。
今陈轩等事事曲从,便为申请,若不施行,即显是朝廷不许,使使臣悦己而怨朝廷,甚非馆伴之体。
右所申都省状,其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详酌指挥事,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
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吏人,乞不上簿。
取进止。
.贴黄。
臣谨按《春秋》:晋盟主也,郑小国也。
而晋之执政韩起欲买玉环于郑商人,子产终不与,曰:“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
又:晋平公使其臣范昭观政于齐,昭请齐景公之觞为寿,晏子不与,又欲奏成周之乐,太师不许。
昭归谓晋侯曰:“齐未可伐也。
臣欲乱其礼,而晏子知之;欲乱其乐,而太师知之。”
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
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谱,亵慢甚矣。
安知非契丹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而陈轩等事事为请,惟恐失其意,臣窃惑之。
又据轩等语录云:高丽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国王捉送上国,乞更赐约束,恐不稳便。
而轩乃答云:“风讯不顺飘过。”
乃是与闽中狡商巧说词理,许令过界。
窃缘私往北界,条禁至重,海外陪臣,犹知遵禀,而轩乃归咎于风,以薄其罪,岂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二)》苏轼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薄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薄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者。
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
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
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
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
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
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
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
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
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曰:“招虞人以皮冠。”
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
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
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
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
伏望圣慈早赐指挥。
取进止。
.贴黄。
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
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
亦合奏知。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苏轼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近再具札子,奏论高丽买书事。
今准敕节文,检会《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前降指挥。
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
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许收买。
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
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
而况《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
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北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
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
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
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
取进止。
.贴黄。
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
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前连元祐七年十一月札)》苏轼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
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望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
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
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
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以上进讫。
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
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事。
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
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运进呈。
伏愿圣慈特赐详览。
若谓所捐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
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
取进止。
.贴黄。
臣所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万一上合圣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挥,大意若曰祖宗旧法,本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乃著令许依例收税,是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宜令今后不问有无旧例,并不得收五谷力胜税钱,仍于课内除豁此一项。
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苏轼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
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
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
是大不然。
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
古者秋分祀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
《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舜之受惮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
柴,祭上帝也。
望,祭山川也。
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
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
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
是大不然。
《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终篇言天而不及地。
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
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
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
故基序曰:“郊祀天地也。”
《春秋》书:“不郊,犹三望。”
《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
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
或曰:“淮、海也。”
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
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
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
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
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
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
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
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
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
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
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于禘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
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
《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
则汉尝合祭矣。
时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为然。
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祗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
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
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
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
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
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
此国朝之礼也。
夫周之礼。
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
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
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
今所行皆非周礼。
三年一郊,非周礼也。
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
效而肆赦,非周礼也。
优赏诸军,非周礼也。
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
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
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
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
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
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玁狁,盖非得已。
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
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
此非臣之所知也。
《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
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
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
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
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
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
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
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
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
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
此又非臣之所知也。
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
此又非臣之所知也。
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
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也?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
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
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
此又非臣之所知也。
《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
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
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
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
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
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
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
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
分而为三,有三不可。
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
军赏不可复加,二也。
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
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
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
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
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
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
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
顾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
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
所贵严祀大典,蚤以时定。
取进止。
.贴黄。
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
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
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苏轼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
臣近奏论圆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
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覆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论可得而定也。
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
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
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
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
若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
取进止。
《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苏轼
元祐八年三月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
臣伏见元祐五年秋颁条贯,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谓于法应赎者。)
无人供侍,子孙居丧者,听尊长自陈,验实婚娶。
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
孟子论礼、色之轻重,不以所重徇所轻,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
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
先王之政,亦有适时从宜者矣。
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
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
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
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男年至于何娶,虽无兼侍,亦足以养父母矣。
今使之释丧而婚会,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岂不过甚矣哉。
《春秋》礼经,记礼之变,必曰自某人始。
使秉直笔者书曰,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祐始,岂不为当世之病乎?臣谨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当时法官有失考论,便为立法。
臣备位秩宗,前日又因迩英进读,论及此事,不敢不奏。
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
稍正礼俗。
谨录奏闻,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