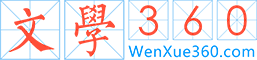两汉经学(东汉和西汉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戴、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
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
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
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
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
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