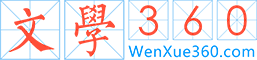战国策·燕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评析
苏秦通过列举尾生、伯夷、曾参的事迹,和一个小故事,驳斥了那些道学家们对他的指责,也说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道学家们实际上不懂政治,正象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从旧道德中分离出来一样,苏秦也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如果政治活动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约,那么政治上将一事无成、毫无作为。国家与个人不一样,国家之间由于无信义可言,就必须讲实力、讲策略、讲变通。国家之间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齿的威逼利诱、暴力欺诈会经常使用,不足为奇。阴谋诡计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俩,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况苏秦等人违背日常道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实战国时期之所以繁荣,战国策士们之所以功勋卓著,在于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们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儒家强调高行节义,但因此导致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充斥官场和社会中,而战国策士们的务实精神为国家增添了活力。善变敢说、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卫道士们,标榜高行节义,却由于囿于教条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处理国际事务,甚至有的虚伪透顶,明里拿道义作攻击人的幌子,暗里玩弄权术诡计、大行尔虞我诈之本领。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害倒是这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