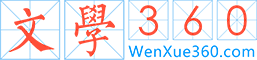《苏轼集》第四十三卷(论十一首)
《孟轲论》苏轼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纲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
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贯之。”
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
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
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首,始终本末,各有条理。
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
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
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
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
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
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
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
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
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
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
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
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
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
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
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
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计。
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
是皆穿窬之类也。”
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
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
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
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
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乐毅论》苏轼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
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
或者之论曰:“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
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
大用则王,小用则亡。
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尝行仁义矣,然终以亡其身、丧其国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
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
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
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
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
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嗟夫!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
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
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
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
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
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
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
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
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
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乐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宽其赋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齐人无复斗志,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奈何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
当战国时,兵强相吞者,岂独在我?以燕、齐之众压其城,而急攻之,可灭此而后食,其谁曰不可?呜呼!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
《荀卿论》苏轼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
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
呜呼!是亦足矣。
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
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
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
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
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
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
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
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
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
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
荀卿独曰:“人性恶。
桀、纣,性也。
尧、舜,伪也。”
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复不逊,而自许太过。
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
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
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
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韩非论》苏轼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
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
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
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
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
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
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
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
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
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
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
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
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留侯论》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
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
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
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
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
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
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贾谊论》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
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
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
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
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
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
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
又皆高帝之旧将。
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
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
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
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
是亦不善处穷者也。
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
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
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
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
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
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
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
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
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
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
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
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
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
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
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霍光论》苏轼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
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
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
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
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
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
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
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
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
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
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
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
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
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
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孙黎民。”
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争之端也。
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
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
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
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扬雄论》苏轼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
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
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
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
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
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
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
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
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
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
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
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
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
是故其论终莫能通。
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
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
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
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
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
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
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
曰:“人之性善恶混。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
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
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
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
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诸葛亮论》苏轼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
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
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
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
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
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
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
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
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
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
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共知也。
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
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
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
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
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
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
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
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韩愈论》苏轼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
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
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
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
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
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
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
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
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
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
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
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
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
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
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
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
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
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
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
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
宜乎愈之以为一也。
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
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
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
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
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
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